鐘偉教授的文章《最低價中標是貌似善舉的惡行》再次引發了大家對于政府采購最低價中標的熱議,對此,余成智主要從最低評標價法的法理依據和實踐價值兩方面進行了辯駁,提出了投標價高低是供應商的一種理性選擇。
筆者認為,對于最低價中標是善舉還是惡行的判斷,首選必須明確是基于道德取向還是結果取向。從政府采購更加注重結果導向,包括追求“物有所值”的發展趨勢來看,應該說結果才是檢驗采購的最終標準。如果供應商投標時動機不純,但在中標后卻能忠實履約,則很難稱之為“惡行”。因此,追溯投標目的并無太大意義,關鍵在于怎么樣避免可能產生的問題。
最低價中標和最低評標價法是兩個概念
最低評標價法和綜合評分法是目前法定的兩種評標方法,其中最低評標價法,是指“最大限度地滿足招標文件實質性要求前提下”,價格最低的投標人中標的評標方法,是一般意義上大家所認為的“最低價中標”。但以最低的價格中標未必就是采取的最低評標價法,也有可能是采用的綜合評分法。如果考慮到目前政府采購80%以上的項目都采用公開招標,而公開招標又基本上都采用綜合評分法,可以認為大部分的最低價中標項目實際是采用的是綜合評標法,采用最低評標價法的競爭性談判和詢價項目在整個政府采購中所占的比例僅10%左右。
而對于綜合評分法來講,本身是對投標供應商價格、技術、資信的全方位考量,不以價格為唯一標準,如果是價格最低的投標供應商中標,只能說該供應商中在綜合比拼中脫穎而出,但他同時也可能是技術最好的,資信最優的,退一步說,即使確實以價格取勝,也說明這個供應商的沒有明顯短板“拖后腿”,是綜合最優的結果。可以說,任何的評標方法都不可能忽視價格因素,而只要有價格因素,就可能是報價最低的供應商中標。
因此,最低價中標與供應商的技術能力、資信水平不是必然的負相關,相反,在采用綜合評分法的情況下,中標本身就在相當程度上體現出了供應商的實力和能力,而不僅僅是價格。并且,最低評標價法僅在政府采購中占據較小比例,未來隨著競爭性磋商方式被更加廣泛的使用,原本使用競爭性談判的項目被分流,采用最低評標價法的項目比例將更低,一些專家以及公眾高估了這一評標方法的影響。
最低價中標只是一個現象而不是問題根源
只要是買東西都可能出現問題,政府采購亦不能幸免,當然政府采購為了抵御風險,有一系列的制度設計,但就我國來說,政府采購的發展仍處于初級階段,采購人的主體責任意識還不強,供應商的誠信經營意識也受到大環境浸染,有法不依和無章可循的情況同時存在,在這樣的背景下,將政府采購本身的很多問題歸咎于最低價中標是有失偏頗的。可以這么說,最低價中標的項目和出現問題的項目屬于兩個集合,兩者確有重合,如果必須對兩者進行關聯,那么更多的是政府采購本身的問題使得最低價中標的概率增大。國外很多發達國家也采用最低評標價法,甚至在一些國家比如美國、日本的使用要遠比我國更加廣泛,但卻沒有出現很大的爭議,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低價不必然導致惡果。因此,最低價中標是某些政府采購項目中的一個現象,并不是政府采購問題的根源,如果舍本逐末,并不能解決鐘教授文中的亂象。
機制上的漏洞才真正值得我們審視
從經濟學的角度上看,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是“經濟人”,追逐利益最大化是天性,所謂的“鉆空子”,如果是在規則范圍內,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選擇,則無可厚非。因此,斥責“不良供應商”鉆空子,包括以低價低質提供產品,首先我們要問的是,他有沒有違反規則,我們有沒有詳細規定要怎么樣的質量,如果沒有,那么肯定是在規則制定或者規則執行時出了什么問題,要從這個方向找原因。對于供應商這一行政相對人,我們要遵循法治思維,“法無禁止即可為”,不能再以行政思維要求市場來迎合我們,對違法違規者要依法查處,但對“鉆孔子”的行為,不妨當做制度規則是否完善的試金石,有缺陷改了就好。不可否認,確實不乏一些機制上的缺失,可能導致中標產品難以達到采購人的預期,并且供應商也以低于預期的價格中標,更確切的講是以低于預期水準的產品中了標。
政府采購要建立對價格不再敏感的免疫系統
那么,怎么樣才能防止達不到預期的產品乘虛而入呢?可以從四個方面著手:
一是正確使用最低評標價法。
根據《政府采購貨物和服務招標投標管理辦法》,“最低評標價法適用于標準定制商品及通用服務項目”,適用范圍有很大限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采用競爭性談判和詢價都必須使用最低評標價法。對于詢價而言“采購的貨物規格、標準統一、現貨貨源充足且價格變化幅度小”的要求,基本包含在最低評標價法的適用范圍以內,但在實際操作中,很多采購代理機構以及采購人都把詢價當做小額采購的自然選擇,而忽視了產品本身的屬性,這點需要注意。對競爭性談判的時候而言,必須考慮除了滿足法定的四種適用情形以外,是否也滿足最低評標價法的適用范圍,滿足法律規定的“技術復雜或者性質特殊,不能確定詳細規格或者具體要求的”和“不能事先計算出價格總額的”的項目,很有可能不是標準定制商品或通用服務,在這種情況下,應該選用其他的采購方式。因此,至少在集中采購中,可以嘗試對采購目錄中哪些品目適用詢價和競爭性談判提出指導性意見,避免錯用。
二是科學展開需求管理。
目前,需求管理中主要有兩個問題與價格息息相關。第一個是觀念的問題,目前全生命周期的理念尚未形成,這個理念直接關系到采購價格,例如在軟件開發的采購中,一些供應商初次投標價格很低,是為了“一只腳先伸進來”,因為日后維護費有很大概率采用單一來源,此時采購單位已經議價空間很小,只能“我為魚肉”,同樣的情況在一些耗材需求量較大的專業設備采購中也有出現。第二是需求表達的問題。我們一直強調的是,采購單位需求不明確,導致了供應商“有機可乘”,從單位主體責任意識的角度看,確認如此。但反過來,我們也要客觀承認,采購單位不是全能的,很多需求即使一些專家都不一定完全清楚,更何況采購單位可能面對各種各樣的采購,自然不可能事事清晰,有單位笑稱,“如果能把需求搞清楚,都變成專家了”,不是沒有道理。也會有人提出,單位可以找專家咨詢或者一些廠家進行調研,但終究也有找不到專家、廠家不愿搭理的情況,這完全可能發生。
因此,對于相對專業、比較復雜的采購,采用非招標采購方式的,由專家制定采購文件是最為理想的方式,但是由于現階段專家水平的良莠不齊,通過隨機方式抽取專家制定采購文件一樣面臨著較大風險。對此,可以依托現有的專家庫,選取部分技術水平、職業素養都達標的專家,作為采購單位需求的咨詢團隊,有需要的采購單位可以自愿自由選擇,只需要在專家抽取環節進行回避即可,這樣可以解決一些單位想要獲得專業支持卻無處可尋的問題。
三是嚴肅合同履約管理。
低價中標的一個可能性是存在“說得好聽卻做不到”的問題,也就是不按采購合同履約,這樣的供應商往往是基于對政府部門驗收水平不高的預計,才敢于試險。而采購單位也存在與需求制定中類似的問題,就是能力不足。對此,采購單位應該事先有充分的準備,一種是可以在代理協議中要求采購代理機構參與驗收,因為代理機構相對采購單位來講比較專業,既有資源,也有經驗,另一種是可以委托有資質的第三方檢驗檢測機構。同時,財政部門需要將履約檢查作為一種“常規武器”,其目的不僅僅是威懾不良供應商,也是倒逼采購單位建立適合本單位、適合特定項目的驗收機制。
四是做好績效評價結果應用。
績效評價作為一種事后的評價手段,雖然對當次采購無法產生影響,但卻可以對未來的采購產生積極作用,是檢驗是否達到“物有所值”的重要手段。從某種程度上來講,績效評價評的是“性價比”,如果“性價比”高,不論價格的高低,都說明這是一次成功的采購,反之,如果“性價比”很低,則要尋找原因,是需求定低了,還是需求出現了偏差或者是預算不合理,通過績效評價對采購進行“溯源”,可以找到問題的原因,而這個原因也往往影響著中標價格。
(陳鋮 浙江省杭州市財政局政府采購監管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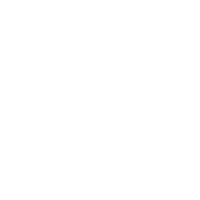 首頁
首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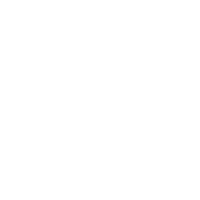 信息公開
信息公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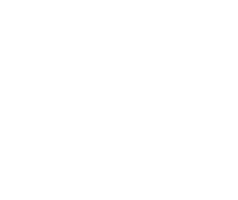 對接網絡
對接網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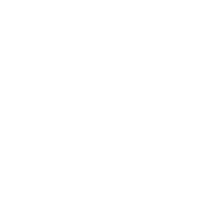 增值服務
增值服務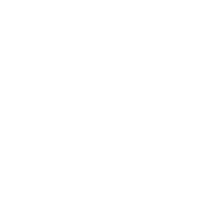 交易智庫
交易智庫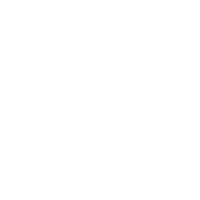 CA互認
CA互認 行業公示
行業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