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回放
2015年10月16日,A公司就某車輛采購項目向采購代理機構提出質疑。質疑事項如下:1.10月12日(周一),在評審現場,采購人確定了中標供應商,直到10月15日才發布結果公告,此舉違反了《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第四十三條的規定;2.采購人在評審現場宣布A公司為中標供應商,10月15日發布的結果公告卻稱“因實質性響應招標文件的供應商不足三家,廢標”,僅僅3天,出現了兩個完全不同的評審結果,質疑采購程序的合法性。
經查,該項目采用了公開招標方式,共有30包,分3天由3組評審專家分別進行評審。其中,第1-10包于10月12日進行評審,第11-20包于10月13日進行評審,第21-30包于10月14日進行評審。招標文件對第5包和第30包投標供應商的實質性資格要求均為“投標人須為所投產品的生產廠家”。
10月12日,第一組評標委員會評審第5包。該包共有A、B、C3家供應商參與投標。評標委員會經評審,推薦A公司為中標候選供應商。采購人當即確認A公司為中標供應商,并現場宣布了中標結果。
10月14日,第三組評標委員會在第30包的評審過程中,通過汽車產品公告及3C認證證書發現B公司并非所投產品的生產廠家,不符合招標文件實質性資格要求,認定B公司投標無效。B公司同時參與了第5包和第30包的投標,該公司對專家的評審提出異議:為什么同一單位,第5包認定資格合格,第30包認定資格不合格?
考慮到第5包的評審可能存在資格性檢查認定錯誤,10月15日,代理機構組織原評標委員會對B公司第5包的投標文件進行了重新評審。經評審,原評標委員會確認,B公司不符合招標文件實質性資格要求“投標人須為所投產品生產廠家”,10月12日的評審存在資格性認定錯誤,認定B公司的投標無效。因此,第5包只有A、C2家單位符合實質性資格要求,實質性響應招標文件的投標人不足三家,作廢標處理。
綜上,A公司質疑所涉第5包的重新評審和廢標結果系由另一投標人B公司的無效投標間接導致。
案例分析
本案中有以下三個關鍵問題,筆者對其一一進行分析。
第一,代理機構統一發布中標、成交結果公告的做法是否合法?
針對A公司的質疑事項1,代理機構解釋稱,采購公告的發布以項目整體為單位,10月12日-10月14日的評審全部完成后,代理機構于10月15日統一發布了整個項目30包的中標、成交結果公告。
《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第四十三條規定,采購人或者采購代理機構應當自中標、成交供應商確定之日起2個工作日內,發出中標、成交通知書,并在省級以上人民政府財政部門指定的媒體上公告中標、成交結果。筆者認為,此處的“中標、成交供應商確定之日”應以包計,而不能以項目計。采購項目一般由采購人、采購代理機構根據采購標的、采購時間進度、資金落實情況等因素設定,可能不分包,也可能分為多個包,通過評審,形成不同的合同項。即,采購是分“包”采,投標是分“包”投,評審是按“包”評,定標當然也是按“包”定。實際上,此處的“包”可看作一個子項目,是整個大的采購項目的組成部分。因此,中標、成交供應商的確定應以包計。當然,還有另一種情形,即某些分包的采購項目中,采購人只確認了其中部分包的采購結果,這時,代理機構應按規定時限發布部分包的采購結果公告,而不能等采購人確認所有包的采購結果后再發布公告。
《民法通則》第一百五十四條明確,規定按照日、月、年計算期間的,開始的當天不算入,從下一天開始計算。據此,筆者認為,本案中第5包的中標供應商確定之日不包括當日(10月12日),應在2個工作日(即10月13日、14日)內發布公告。
有人提出,《條例》第四十三條規定的是“中標、成交結果”,而第5包是廢標結果,是否仍適用“2個工作日”的限制?2個工作日內發生了本案中提到的變故,在明知第5包的評審存在問題的情況下,是否仍應按此條規定發布“中標、成交結果”公告?
對此,筆者的理解是,單從目前法律的規定看,廢標結果公告確實不適用2個工作日的限制。但是,公告采購結果是政府采購公開透明原則的重要體現。而且根據《政府采購法》的要求,采購人應當將廢標理由通知所有投標人。鑒于此,筆者認為,無論項目采購活動是否成功,采購人、采購代理機構均應按照法定時限公告采購結果。當然,在“2個工作日”內,發現有評審錯誤、存在可以重新評審的事項的,評審結果可能會被改變。在此情況下要求代理機構繼續公告中標、成交結果,確實不妥。
綜上,筆者認為,部分分包較多、評審時間較長的項目,應以單個分包的中標、成交供應商確定之日為準,分包分批公告中標、成交結果,否則便違反了《條例》第四十三條的規定。
第二,代理機構組織重新評審,是否合法?
我國政府采購法律法規對重新評審持嚴格限制、禁止態度。《條例》第四十四條明確,除國務院財政部門規定的情形外,采購人、采購代理機構不得以任何理由組織重新評審。可重新評審的除外情形,在《財政部關于進一步規范政府采購評審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財庫〔2012〕69號)、《政府采購非招標采購方式管理辦法》(財政部第74號令)和《政府采購競爭性磋商采購方式管理暫行辦法》(財庫〔2014〕214號)等部門規章中均有提及。筆者歸納如下表:
概括言之,就是在專家評審存在特定錯誤的情況下,可組織重新評審,糾正錯誤。值得一提的是,69號文規定,出現上述除外情形的,“評審委員會應當現場修改評審結果,并在評審報告中明確記載”。也就是說,對評審結果的修改應當是在“現場”進行的。那么,評審活動完成、評審委員會已解散后發現除外情形,是否也可組織重新評審?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釋義》在關于《條例》第四十四條的解釋中,將69號文規定的現場修改評審結果定義為“評審中的復核”,同時明確,復核應在評審結果匯總完成后至評審報告簽署完成前進行。而“重新評審”則指簽署了評審報告、評審活動完成后,原評標委員會、談判小組、磋商小組和詢價小組成員對自己評審意見的重新檢查。筆者認為,《釋義》對69號文的規定作了擴大解釋,明確在復核階段發現除外情形的,應當現場修改評審結果;如在評審結束后發現,則可組織重新評審。
具體到本案,B公司不是所投產品的生產廠家,不符合招標文件實質性資格要求,卻被認定為合格標,確實屬于“資格性檢查認定錯誤”。在第5包的評審活動完成后,代理機構和另一組評審專家發現存在錯誤,進而組織原評標委員會重新評審、修改結果。根據上述規定及《釋義》中的解釋,筆者認為,代理機構組織重新評審的做法是合法的。
第三,處理質疑時,原評標委員會對相關供應商投標文件的重新檢查,是否屬于重新評審?
重新評審的除外情形往往通過供應商提出質疑,由采購人、采購代理機構、財政監督部門在調查過程中發現。本案系由后一組專家發現前一組專家存在資格審查認定錯誤,由采購人、采購代理機構發起重新評審。而發現除外情形更多、更重要的途徑是質疑處理。
質疑是《政府采購法》為供應商提供的重要救濟程序。《條例》第五十二條規定,政府采購評審專家應當配合采購人或者采購代理機構答復供應商的詢問和質疑。代理機構處理質疑的常用程序就是組織原評標委員會就質疑事項出具意見。而這一程序往往包含原評審專家對相關供應商投標文件的重新檢查,那么,這種重新檢查是否可理解為重新評審?通過答復質疑改變了采購結果,是否也屬于某種意義上的重新評審?
從《條例》的立法精神來看,除了以上列出的除外情形外,不允許重新評審。一方面,政府采購法律規定專家名單保密、評審場所保密、評審情況保密。這與公開透明原則似乎相違背。但種種保密的目的在于保證第三方專家在最小程度的干擾下,依法、公平、公正、客觀地發表專業性意見,為采購人推薦優秀的候選供應商。這種保密制度設計是為了更大程度上的公平、公正。但是,重新評審往往是在專家名單公布、評審結果確定后進行的。重新評審首當其沖面臨的是難以規避的法律風險。與重新開展采購活動相比,重新評審看似節省了前期采購時間和資源,實則給采購人、代理機構埋下隱患:法律程序未作規定,投標供應商不認可。而且,在目前評審專家責任難以追究的情況下,最終的法律后果只能由采購人、代理機構承擔。另一方面,實踐中,個別采購人、代理機構對評審結果不滿意,尋找各種理由組織重新評審,借以推翻原評審結果。不嚴格限制重新評審,將嚴重損害政府采購的公信力,導致“尋租”行為增加,腐敗滋生。
從這一角度來看,筆者認為,質疑處理過程中,原評審專家對相關供應商投標文件的重新檢查,不屬于重新評審。重新評審是就投標的所有問題重新進行審查;而重新檢查是僅針對質疑對象進行的局部審查,且應限于質疑問題,不能因此及彼。質疑答復可能改變原評審結果,但這種改變是在原評審推薦結果的基礎上進行的,不能理解為重新評審。對于質疑處理中發現專家未按評審標準進行評審、影響評審結果的,筆者不主張采購人、代理機構要求專家糾正錯誤,而是建議采購人、代理機構在核實情況的基礎上,向財政監督部門報告,由財政部門依法審查評審活動,依法糾正錯誤。
不可否認,當前,部分供應商的質疑發生了異化,正當的供應商救濟制度演變成個別采購人的救濟制度。即,一旦評審結果不是采購人預想的,采購人便與暗定的供應商聯合起來,由供應商提起質疑,達到改變評審結果的目的。面對層出不窮的質疑問題,組織專家協助處理質疑,成為采購人、代理機構的一項重要工作,但在此過程中應明確權責,不能讓處理質疑成為個別采購人要求的重新評審。
法規鏈接
《民法通則》第一百五十四條
《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四條
《財政部關于進一步規范政府采購評審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
《政府采購非招標采購方式管理辦法》第二十一條
《政府采購競爭性磋商采購方式管理暫行辦法》第三十二條
(羅婭天津市政府采購中心)
本網擁有此文版權,若需轉載或復制,請注明來源于“中國招標投標公共服務平臺”及原文鏈接,并保持文章的完整性。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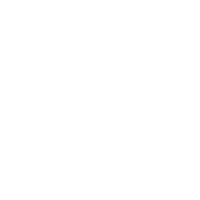 首頁
首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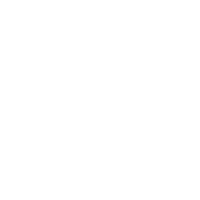 信息公開
信息公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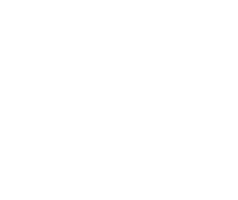 對接網絡
對接網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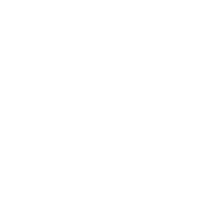 增值服務
增值服務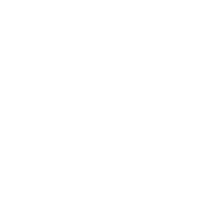 交易智庫
交易智庫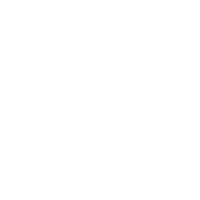 CA互認
CA互認 行業公示
行業公示


